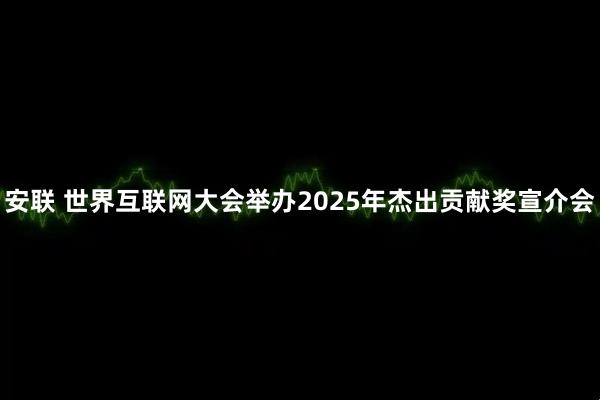库东投资
库东投资
游走于东江密布的水网,扒龙舟,是东莞水乡古老而热烈的节令运动。临近端午,新龙陆续“骏水”,龙舟队重启训练,江面上鼓声震动,龙头昂扬。
远早于此,龙头工匠黄智冬的忙碌始于年初。到农历四月中旬,他已经利用本职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,雕刻完成了十余只龙头。

黄智冬为东坑丁屋村制作的龙头,装上了新龙船,近日举行了下水仪式。
黄智冬生于2002年,今年23岁,是东莞本地手工龙头师傅中最年轻的一个。他主理的“大冬向龙头工坊”,藏在万江街道黄屋基村的一条老巷子里。
自建房的一层车库被改成工作室,木料堆在门边,桌子朝外,案板靠墙。空气里有油漆未干的气味,混着香樟木刚起刀的粗粝清香。
两只新龙头正搭在小凳上等待上色,几只送来复刻的老龙头在一旁整齐码放——它们有的将亮相镇街的龙舟趁景活动,有的则将在广州、佛山等地登船。

“要不试一下”
黄智冬是土生土长的万江人,幼时常跟着父亲到东江边看龙舟比赛。别人看的是水上厮杀,他就只盯着船上的龙头看,观察它们不同的样式、颜色和神态。
龙头不仅是龙舟的“脸面”,也是辨认队伍最直观的标志。在没有统一服装和桨板装饰的年代,只需通过龙头,人们就能分辨是哪条村、哪只船。

2024年,万江“东莞龙舟第一景”。
“睇”完龙舟回到家,黄智冬会把记住的图案一笔一画描在纸上,“我当时就是喜欢画画,画得多了、久了,渐渐知道哪里对、哪里不对。”
比如,眼睛是不是太靠上了,鼻梁线条弯得自然不自然,嘴巴开口的角度符不符合龙的神气。没有人教,他就在一张张草图中不断琢磨。
小学五六年级时,黄智冬试着将龙头侧脸誊在一小块木头边角料上,用一把美工刀一点点削出轮廓,慢慢地挖出眼窝、鼻子、牙齿。“只是想着要不试一下,没想到真的刻出了像样的形状。”他说。

龙头模型半成品库东投资。
2015年,黄智冬读初二时,在朋友圈发布的一件模型作品引起了一位广州龙舟爱好者的注意。对方主动联系他,提出:“要不试着给我做一个?”
他答应下来,特地找到一块香樟木,从画线、开刀,到打磨、上色,完全凭借自己的构思和实践完成,“现在回头看,觉得不够好,但也算是我接到的第一个正式单。”
此后,黄智冬陆续接到一些龙头模型订单。他一边学着画图纸、量尺寸、分段雕刻、调色上漆,一边在反复试错中慢慢磨出了手感,也将“爱好”一点点磨成了“技艺”。

黄智冬制作的龙头模型。
四年后,又是那句熟悉的“要不试一下”。这一次,来询问的是万江拔蛟窝社区,他们计划打造一个全新的龙头。经人推荐下,订单落到了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黄智冬手中。推荐人也劝他:“要不试一下。”
这是他第一次雕刻真正要“上船”的大龙头,整只龙头长76厘米、宽18厘米,重量超过30斤。与之前的模型龙头相比,它不仅结构更复杂,还承载着整个社区的期望。

黄智冬为拔蛟窝社区制作的龙头,用在赛龙舟战船上。
黄智冬花了好些天画图纸,与社区反复推敲细节。雕刻阶段,他既兴奋又紧张,几乎每天都跟龙头待在一起,粗雕、精雕,打磨、抛光,再按社区要求配色上漆。
那年五月初一,是万江扒标的大日子。黄智冬站在人群里,看着自己雕刻的龙头被稳稳地装在拔蛟窝社区的战船上。鼓声响起,龙舟入水,他的作品第一次真正“游”了起来。

“龙头神秘又复杂”
谈起对龙头的兴趣,黄智冬总是提到某种始终未曾消散的“神秘感”。
在他的童年记忆里,龙头并不能常常见到。每年只有端午前后的一两个月,龙头才会被“请”出,与同样沉睡一年的龙舟“合体”,村民们才得以一窥真容。其余时间,它都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,安置在庙宇祠堂,仿佛不能被随意惊扰的神明。

起龙仪式前,需要先将龙头“请”出。
小时候的敬畏与好奇,延续到了现在。如今,黄智冬在每一刀里,都试图留住那股“神秘”的精气神。
龙头由额头、眼睛、嘴唇、牙齿、龙角、龙鳞等部位组成,其中他最在意的,是眼窝。“我对这个位置比较敏感。”黄智冬说着,指向一只刚雕完的龙头,“我做的龙头,眼窝会刻得比较深,看起来眼睛大一点,神气也就出来了。”
 库东投资
库东投资
黄智冬和他制作的龙头。
雕刻时,他会先轻轻勾勒出眼窝的线条,然后用凿子一点点刮深。每处理完一两个细节,他都要停下工具,后退两步,从不同角度打量神态。
老师傅们说,一个好龙头,既要有“形”的准确,也要有“神”的传达。“为什么是这个形状?为什么有的龙头不怒自威,有的却带着笑意?”这些问题,黄智冬在雕刻中反复自问。

黄智冬制作的新龙头和龙头模型。
“木雕其实是用减法的方式做表达。让它温和,还是让它有气势,都得靠你自己理解,然后通过线条表现出来。”在他看来,龙头的神态不是凭空而来,而是从线条和形状的拿捏、比例的推敲中慢慢刻画出的情绪与性格。
手艺渐熟之后,黄智冬也慢慢摸索出各地龙头造型背后的逻辑。他介绍,不同流域的水文环境,影响着龙头的造型风格。
东江流域多使用造型宽厚饱满的“大头狗”,配合较大的船身,适合在水面宽阔、波浪大的江面航行;而西江流域则多使用“鸡公头”样式,造型干练、结构更轻巧,便于在浅窄、弯多的河涌中穿行,能够减少碰撞风险。

黄智冬在为“大头狗”上色,身后为“鸡公头”。
更细致且复杂的差异,则体现在龙头的色彩搭配、细节处理与村落信仰的对应上。红脸龙头若配长须,象征威严,常见于信仰关公的村落,没有胡须、神态温和的,则多用于供奉观音、天后等女性神明;黑面黑须的龙头形象刚硬,通常对应北帝等水神信仰。
在黄智冬接过的订单中,万江拔蛟窝社区信奉华光大帝,属火神兼财神,村民要求龙头必须以红、金、黑为主色;麻涌川槎村的“天后”龙头鼻子卷曲,色彩鲜红艳丽;来自广州新塘的一个复刻龙头主色为橙色,象征着其信仰的九天玄女。

黄智冬为麻涌川槎村制作的龙头。

“找回耐看的味道”
2023年,黄智冬为万江社区设计了一款创新的龙头。“其实是我先有的灵感,龙头的样子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。我觉得它就应该长这样。”
他将图纸拿给龙舟队看,对方很支持。黄智冬被授予全权创作的空间:红绿主色调不变,颈部雕上“连心锁”的图案,象征社区队员团结一致,龙角则首次尝试鱼形镂空设计,取意“鱼跃龙门”。

黄智冬为万江社区制作的龙头。
但更多时候,黄智冬需要反复揣摩老一辈师傅的用意与思路。“新设计一个龙头,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;而复刻老龙头,是在传达上一代人的审美和理解。”
“这个地方,他当年是怎么刻的,为什么要这么刻?我能不能按照原样刻出来?还是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还原?”这样的思考与取舍,黄智冬在复刻龙头的过程中时常经历。
去年,常平岗梓村打算恢复停办二十多年的龙舟活动,请他重制两只龙头。但老龙头的模样,只存在于一张模糊的老照片里。
黄智冬为此专程跑去村里拜访,将村民们的只言片语拼在一起,尽可能还原出龙头旧时的模样。游龙那天,不少村民站在岸边感叹:“这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岗梓龙头模样没什么区别,红彤彤的,看着就喜庆。”

黄智冬为常平岗梓村复刻的龙头。
黄智冬最偏爱的,也正是这种手工老龙头。他说,小时候痴迷的龙头样式已经在脑子里定了型,而那一代师傅却相继离世。他想做的,就是不断找寻那种“很朴素,但特别耐看,怎么看都不腻”的味道。
目前,黄智冬的主业是一名小学模型课教师,雕刻龙头只能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完成。他估算,一只龙头从选料到上色,平均要十天左右,超八成工序依赖手工。“按照一天8小时的手工成本计算,几乎没有多少利润。”

黄智冬在雕刻木料。
但比赚钱更难的,是技艺的接力。黄智冬坦言,入行的年轻人极少,在坚守的大多是上年纪的老师傅。他曾向中堂的前辈请教,但大多数时候,还是靠自己琢磨。“很多人会划龙舟、看龙舟,但龙头的讲究,好像越来越少人能说得清。”
这两年,黄智冬看到了一些变化。东莞多次举办老龙头展主题展,普及“乡乡各异”的龙头文化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与龙头相关的文创产品,造型生动、价格亲民。这些尝试,让更多人对龙头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。

2025年东莞龙舟月期间举办的“老龙头”主题展。
如今,黄智冬也还会做些手工模型对外售卖。他期待,大家在关注龙舟赛事、感受节日热闹的同时,也能顺着目光,多看几眼龙头——那里藏着龙舟的性格和来处。
采写:南方+记者 王颖 何绮莹
摄影:何绮莹 麦晴怡
视频:何绮莹
设计:孙沛川
部分图片由受访者、万江宣提供库东投资
淘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